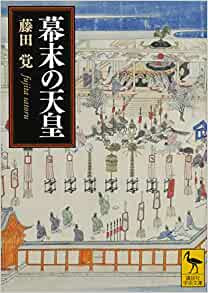眾所周知,「敬天愛人」是西鄉隆盛的座右銘。在東京上野公園那尊有名的西鄉銅像的旁邊,豎立著一塊介紹銅像由來的雲石碑,頂端便寫著「敬天愛人」四個大字。在很多地方,「敬天愛人」就如同西鄉本人一樣,獲得人們的尊敬,製成橫幅掛在當眼的地方,時刻提醒自己毋忘這做人的信條。
2021年2月24日 星期三
2021年2月4日 星期四
2021年1月19日 星期二
2023年大河劇《どうする家康》
今天日本NHK初步公布了2023年大河劇劇目及主角。
劇名暫定為「どうする家康」(暫譯:家康怎麼辦?),由古澤良太(代表作有「相棒」系列、「王牌大律師」系列、「信用詐欺師」等等)負責劇本,由人氣偶像團體「嵐」成員松本潤飾演主人公德川家康。
2021年1月13日 星期三
《約翰万次郎傳奇一生》
書名:約翰‧万次郎傳奇一生
作者:陳新炎
出版社:允晨文化
不經不覺,我移居台灣已經兩個月了。生活尚未有著落,娛樂不多,唯一不用花錢又符合我興趣的活動,當然就是跑圖書館啦。
據我不正確的觀察,台港兩地圖書館所進的書不盡相同,台灣這邊英文書似乎比香港少,相反,有些中文書是香港圖書館沒有存庫的。像今天介紹這一本,香港書店和圖書館是一本都沒有進。沒想到來到台灣之後,竟然讓我挖到寶。
2021年1月4日 星期一
《吉田松陰與近代中國》
書名:吉田松陰與近代中國
作者:郭連友
出版社: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
這是一本中國人寫的關於吉田松陰的書,作者郭連友教授是中華日本哲學會副會長、中華日本學會理事、日本思想史學會會員,研究領域是日本思想史、日本文化史,以及中日思想交流史。
所以可以想見,郭教授這本書是以吉田松陰予中國晚清志士的影響為主軸的。
2020年12月24日 星期四
幕末的天皇
最近在拜讀藤田覺的《幕末の天皇》。
這是我們研讀幕末維新史時很容易忽略的一塊。包括拙作《幕末長州》在內,敘述幕末史的華文書籍中,大多把幕府視作政治主體,然後將一連串動亂歸因於幕府的失政,相對地把維新志士與朝廷拉在一起,仿佛是維新志士替朝廷打倒幕末,將政權收回朝廷掌中。「大政奉還」、「王政復古」這兩組詞語,正是這種觀點的反映。
2020年11月18日 星期三
年號戰爭——以永祿、天正改元為例
在中華文化圈的世界,年號不只用作紀年,而且是權力合法性的象徵;使用一個年號,代表著從屬於那個政權,願意接受那個政權的管治。日本在明治時代實行一世一元制以前,經常出現更改年號的情況,有時候一個天皇在位期間,會多次更換年號,僅有少數的天皇只用上一個年號。更換年號多數是因為下列情況:
1.天皇踐祚
2.出現天災異變,例如地震、火災、瘟疫
3.逢革命之年,即辛酉革命、甲子革令(辛酉年後的第四年)
除了天皇踐祚之外,以上原因看似是不可抗力,但實際的改元操作上也涉及許多人為因素,特別是戰亂時期,改元更淪為權力者的政治鬥爭工具。以下以戰國時期永祿、天正兩個年號為例子,簡單介紹這兩場充滿張力的年號戰爭。
2020年10月11日 星期日
再談穢多、非人
近日重讀網野善彥教授寫的《重新解讀日本歷史》(聯經出版),書中第三章專門談論穢多、非人這些受歧視的群體,有些想法想要記錄下來。
網野善彥開宗明義提出,南北朝前後的十四、十五世紀,是日本社會大變革期,許多現代社會的觀念都是從這個變革期產生的,以前的社會跟我們所想像的截然不同(想起內藤湖南說應仁之亂以前的日本史都是外國史)。
2020年9月15日 星期二
2020年9月2日 星期三
再談福澤諭吉
福澤諭吉之所以受日本人敬愛,是因為他向尚未接觸國際社會的日本人介紹西洋文明。他在幕末時曾隨幕府前往美國,回來日本便寫了一本《西洋事情》,不計蘭學的話,他可說是最早一批向日本人展示西洋文化的人。他不把這些知識當做是很珍貴的秘笈,反而很積極推廣,希望啟迪日本人的見聞和智慧。當時新舊時代交替,日本尚在萌芽發展階段,而西方列強對東亞虎視眈眈,福澤便透過《西洋事情》和稍後的《勸學篇》來激勵日本人勤奮自學,只要每個人都努力學習,便可有獨立的人格,進而使日本有獨立的國格,與世界列強為伍。這既是他身為下級藩士受盡白眼的經驗,也是當時日本面對國際社會的處境。
《勸學篇》第一句「天不生人上之人,亦不生人下之人」,看似是說人無貴賤之分,人人生而平等,就像美國獨立宣言那句名言一樣;但對比他在甲午戰爭時稱清兵為「豚尾兵」、「惡獸」的表現,便知道不是這麼一回事。我對這一句話的解讀,是世界雖然有文明的國家也有落後的國家,但上天賦了人類的質性其實是一樣的,每個人都可以透過後天的努力成為人上人,相反若不努力改變自己,便會淪為人下人,福澤諭吉以此勸勉日本人獨立自強,使日本成為比別國優秀的國家,這正是《勸學篇》的主旨。
他對於落後的人是很歧視的,絕不是平等主義者。就像當時已流行的祟洋風潮,福澤也不能免俗,相信人種有優劣之分,支持「人種改良論」,認為日本人應該模仿家蓄品種改良,挑選優秀父母(指文明的歐美人)誕下優秀後代。他這種思想似乎在知識界亦十分普遍,在他的《時事新報》擔任記者的高橋義雄撰寫了《日本人種改良論》,提倡與西方人雜婚,便是基於此一優勝劣敗的思想。後來福澤諭吉的《脫亞論》也是由此而來,因為失敗的朝鮮人和中國人都是東亞劣等民族,他不屑與落後的東亞為伍(脫亞不等於入歐,這一點需要注意)。
要知道,福澤的《西洋事情》、《勸學篇》抑或《脫亞論》,對象都是日本人。他絕不是要把他的思想推廣到全世界成為普世價值。相反,我們更要留意當時世界的思潮。當時是民族主義和達爾文主義流行的年代,是帝國侵略、弱肉強食、適者生存的年代,不是自由、平等、博愛的年代。我們看福澤的作品,了解他的人品,不能撇開時代脈絡。